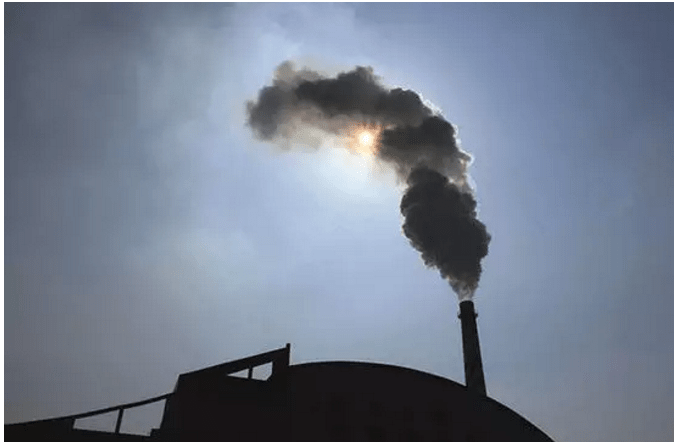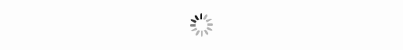導(dǎo)讀:生活垃圾焚燒在我國(guó)面臨著實(shí)實(shí)在在的現(xiàn)實(shí)危機(jī),除常規(guī)污染物排放不達(dá)標(biāo)及灰渣違法處置這些常見(jiàn)問(wèn)題外,其二惡英和汞污染風(fēng)險(xiǎn)已經(jīng)不容忽視。從借鑒發(fā)達(dá)國(guó)家經(jīng)驗(yàn)教訓(xùn)及可持續(xù)發(fā)展的角度看,垃圾焚燒不能成為應(yīng)對(duì)垃圾問(wèn)題的優(yōu)先對(duì)策,而我國(guó)目前整體及局部地區(qū)的環(huán)境容量也不允許焚燒規(guī)模的繼續(xù)擴(kuò)張。在介紹這些基本形勢(shì)的同時(shí),本文提議政府部門、民間組織、普通公眾合力加強(qiáng)對(duì)垃圾焚燒的監(jiān)督,有目標(biāo)、有計(jì)劃地逐步擺脫對(duì)垃圾焚燒的依賴。

作者:毛達(dá)(環(huán)境史博士,北京零廢棄運(yùn)動(dòng)發(fā)起人)
近幾年來(lái),許多地方的公眾都質(zhì)疑或反對(duì)垃圾焚燒廠項(xiàng)目的規(guī)劃和建設(shè),也有很多已經(jīng)建起運(yùn)營(yíng)的焚燒廠遭遇周邊居民的持續(xù)投訴或抗議。為何政府官員和技術(shù)專家口中的“現(xiàn)代化垃圾處理技術(shù)”如此不受公眾待見(jiàn)?撇開(kāi)那些“安全無(wú)憂”的空洞說(shuō)理,焚燒廠已經(jīng)出現(xiàn)的種種污染問(wèn)題,以及有悖于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特性急需社會(huì)各界的正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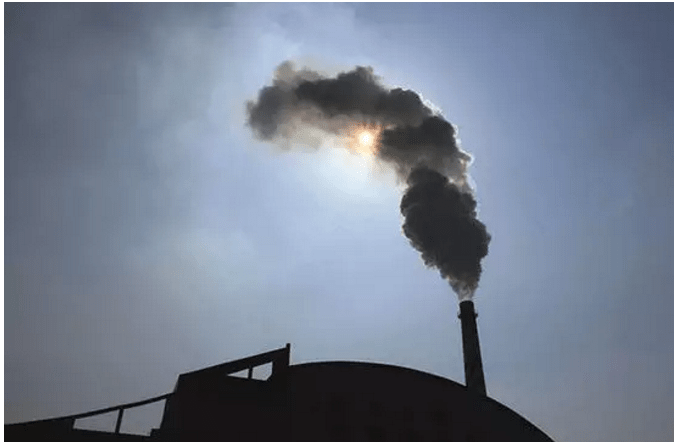
不可忽視的現(xiàn)實(shí)危機(jī)
如許多人所知,垃圾焚燒排放出來(lái)的污染物非常多,但目前由《生活垃圾焚燒污染控制標(biāo)準(zhǔn)》直接管控的僅有10種,既包含常規(guī)污染物,如:煙塵、一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氯化氫等,也包含一些特征污染物,如持久性有機(jī)污染物二惡英和重金屬汞。
對(duì)反對(duì)焚燒的公眾而言,二惡英無(wú)疑是最讓他們敏感的,而許多科研信息或政府公開(kāi)數(shù)據(jù)也證實(shí)這些擔(dān)憂不無(wú)道理。
首先看看我國(guó)垃圾焚燒行業(yè)二惡英的總體污染形勢(shì)。2009年,中國(guó)城市建設(shè)研究院學(xué)者發(fā)表論文稱,2007年中國(guó)全國(guó)生活垃圾焚燒廠(60至70座)的估算二惡英大氣排放量為157.93 g TEQ(毒性當(dāng)量),相比2004年的估算量125.8 g TEQ,已有顯著增長(zhǎng)。與此相比較,德國(guó)1994年生活垃圾焚燒的二惡英大氣排放量?jī)H為30 g TEQ,進(jìn)入21世紀(jì)后(共60多座),年排放量估計(jì)降至0.5 g TEQ以下。
有專家認(rèn)為,隨著技術(shù)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國(guó)垃圾焚燒行業(yè)的二惡英排放會(huì)逐步降低,但這樣的觀點(diǎn)沒(méi)有考慮該行業(yè)垃圾處理總體規(guī)模的急劇增大,可能會(huì)抵消技術(shù)水平提高帶來(lái)的減排效果,甚至使問(wèn)題更趨惡化。
對(duì)于普通公眾而言,要準(zhǔn)確預(yù)測(cè)焚燒廠的二惡英污染風(fēng)險(xiǎn),目前幾乎是不可能的,因?yàn)闊o(wú)論是焚燒廠自身還是監(jiān)管它們的政府部門都極少主動(dòng)公開(kāi)相關(guān)信息;即便遇到公眾申請(qǐng),也是千百般地回避或拒絕。2012年,環(huán)保組織蕪湖生態(tài)中心曾先后向全國(guó)31個(gè)省/直轄市、76個(gè)市/區(qū)級(jí)環(huán)保局,針對(duì)全國(guó)122 座在運(yùn)行垃圾焚燒廠的污染控制情況進(jìn)行信息公開(kāi)申請(qǐng),結(jié)果只獲得42座廠的排放監(jiān)測(cè)數(shù)據(jù),而且其中僅有10座廠的二惡英排放數(shù)據(jù),占總體的8%。
如此之多的公共信息缺失,也并不完全因?yàn)橄嚓P(guān)部門的不情愿。在2012年底一起環(huán)境信息公開(kāi)行政訴訟案的審理過(guò)程中,被告廣州市環(huán)保局承認(rèn):它們之所以不公開(kāi)廣州李坑焚燒廠的一部分二惡英排放信息,是因?yàn)?009年以前根本就沒(méi)有監(jiān)測(cè)。
雖然可獲得的信息有限、數(shù)據(jù)有限,一些科研文獻(xiàn)還是讓公眾可以窺見(jiàn)我國(guó)垃圾焚燒廠二惡英污染問(wèn)題的冰山一角。2009年,幾位中國(guó)科學(xué)院學(xué)者發(fā)表了他們對(duì)中國(guó)19座生活垃圾焚燒廠二惡英大氣排放水平的研究,結(jié)果表明,有13座達(dá)不到歐盟0.1 ng TEQ/m3的標(biāo)準(zhǔn),有3座甚至超出我國(guó)舊的1 ng TEQ/m3的國(guó)家標(biāo)準(zhǔn)。而對(duì)于一直處在風(fēng)口浪尖的廣州李坑焚燒廠,廣州城管委曾夸下海口稱其二惡英排放能達(dá)到歐盟標(biāo)準(zhǔn),但實(shí)際被迫公開(kāi)的數(shù)據(jù)卻顯示不能達(dá)到。
焚燒廠導(dǎo)致周邊環(huán)境二惡英污染,也是有據(jù)可循的。2008年,上海市檢測(cè)中心研究者發(fā)表論文,報(bào)告上海嘉定某焚燒廠周邊土壤中二惡英含量明顯高于背景土壤的水平,于是得出結(jié)論:焚燒爐是上海地區(qū)土壤中二惡英污染的一個(gè)來(lái)源。2013年12月,溫州市環(huán)保局罕見(jiàn)地公開(kāi)了該局對(duì)當(dāng)?shù)匾蛔贌龔S的二惡英排放和污染情況進(jìn)行監(jiān)督性監(jiān)測(cè)的信息,結(jié)果表明,雖然煙氣排放數(shù)據(jù)達(dá)到國(guó)家標(biāo)準(zhǔn),但焚燒廠周圍有一處地點(diǎn)大氣二惡英水平達(dá)3.98 pg TEQ/m3,已嚴(yán)重超過(guò)我國(guó)環(huán)境影響評(píng)價(jià)政策對(duì)垃圾焚燒廠二惡英污染影響預(yù)測(cè)的限值規(guī)定(等同于日本目前的大氣二惡英濃度限值)。
就在不少政府官員和技術(shù)專家忙于給垃圾焚燒廠二惡英污染去“妖魔化”的時(shí)候,這個(gè)行業(yè)的汞污染防治壓力也在悄然增加。
總體而言,垃圾焚燒行業(yè)已被證明是人為汞排放的主要污染源。根據(jù)華南理工大學(xué)學(xué)者2011年發(fā)表的一篇論文,生活垃圾焚燒的汞排放量占珠江三角洲人為總排放量的21%,僅次于燃煤排放(28%)。另一項(xiàng)由Dan Hu等人在2012年發(fā)表的論文顯示,自2004至2010年,我國(guó)城市固體廢棄物燃燒的汞排放量從每年0.9噸增長(zhǎng)到了6.1噸,平均增長(zhǎng)率達(dá)37.3%。
如果將失控的汞排放總量分解到具體的垃圾焚燒項(xiàng)目上,情況同樣也是嚴(yán)重的。如許多人所知,今年環(huán)保部和國(guó)家質(zhì)檢總局聯(lián)合發(fā)布了修訂后的《生活垃圾焚燒污染控制標(biāo)準(zhǔn)》。值得注意的是,標(biāo)準(zhǔn)的二次征求意見(jiàn)稿曾一度將汞排放限值由一次征求意見(jiàn)稿中向歐盟看齊的0.05mg/m3放松至0.1mg/m3(舊國(guó)標(biāo)限值為0.2mg/m3)。最終,在各方壓力之下,才又恢復(fù)至一次征求意見(jiàn)稿、即歐盟標(biāo)準(zhǔn)的水平。
根據(jù)環(huán)保部發(fā)布的上述標(biāo)準(zhǔn)二次征求意見(jiàn)稿的“編制說(shuō)明”,編制單位調(diào)查了國(guó)內(nèi)20座生活垃圾焚燒廠的煙氣汞排放水平,如果參照現(xiàn)行標(biāo)準(zhǔn),僅14座能夠達(dá)標(biāo),如果參照二次意見(jiàn)稿標(biāo)準(zhǔn),則有18座可以過(guò)關(guān)。由此可見(jiàn),環(huán)保部之所以在汞排放限值的制定上反反復(fù)復(fù),實(shí)則是我國(guó)垃圾焚燒廠汞污染防治的客觀嚴(yán)峻形勢(shì)所致。
與二惡英問(wèn)題一樣,垃圾焚燒廠已經(jīng)給周邊帶來(lái)了實(shí)實(shí)在在的汞污染。2005年,湯慶和等發(fā)表學(xué)術(shù)論文,報(bào)告上海浦東生活垃圾焚燒廠周邊環(huán)境的土壤汞污染水平呈增加趨勢(shì),下風(fēng)口土壤及大氣汞污染水平都較其他方位明顯高。2009年,趙宏偉等發(fā)表學(xué)術(shù)論文,認(rèn)為深圳市清水河垃圾焚燒廠周圍的優(yōu)勢(shì)植物均受到一定程度的汞污染,而且與焚燒廠的污染物排放有直接關(guān)系。2013年,華南理工大學(xué)學(xué)者發(fā)表論文,顯示廣州李坑焚燒廠周邊土壤、水體及植物都受到輕度至中度的甲基汞污染,且變化趨勢(shì)與焚燒廠運(yùn)營(yíng)時(shí)間有一定的聯(lián)系。
以上討論的僅是我國(guó)垃圾焚燒廠排放出來(lái)的兩種最有害物質(zhì)的污染情況,其他一些常規(guī)大氣污染物的控制及灰渣的污染防治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問(wèn)題。例如,本不應(yīng)該出現(xiàn)在焚燒廠廠界內(nèi)外的高濃度惡臭氣體,卻成了各地居民反復(fù)投訴的公害。一些公開(kāi)的污染監(jiān)測(cè)數(shù)據(jù)——盡管非常有限——顯示某些焚燒廠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等常規(guī)污染物超標(biāo)情況嚴(yán)重。此外,近期媒體和公眾陸續(xù)揭露了不少焚燒廠飛灰非法處置的問(wèn)題,一位垃圾焚燒行業(yè)內(nèi)專家也坦陳,全國(guó)范圍內(nèi)這種危險(xiǎn)廢棄物得到妥善處置的比例可能只有一半。更讓人擔(dān)憂的是,對(duì)于那些彌漫著惡臭、經(jīng)常超標(biāo)排放、違法傾倒廢物的焚燒廠,各地的政府監(jiān)管部門卻鮮有采取措施果斷關(guān)停、整改、處罰的,公眾對(duì)于這樣的一種污染行業(yè)及其監(jiān)管部門投以極不信任的態(tài)度是很自然的。
垃圾焚燒沒(méi)有繼續(xù)發(fā)展的空間
垃圾焚燒這個(gè)行業(yè)要繼續(xù)擴(kuò)充、發(fā)展,得具備兩個(gè)條件。一是源源不斷可供其處理的垃圾,二是環(huán)境容量足夠消納其產(chǎn)生的污染物。現(xiàn)實(shí)中,這兩點(diǎn)都可能對(duì)垃圾焚燒發(fā)展構(gòu)成障礙。
時(shí)間若倒退大概30年,在填埋處于垃圾處理技術(shù)統(tǒng)治地位的時(shí)代,我國(guó)環(huán)衛(wèi)工程界就已經(jīng)開(kāi)始向往有朝一日能夠趕上西方發(fā)達(dá)國(guó)家的先進(jìn)步伐,用焚燒“消滅”垃圾。當(dāng)時(shí)之所以遲緩,不過(guò)是因?yàn)槲覈?guó)的垃圾組分及經(jīng)濟(jì)實(shí)力還不能支撐焚燒的發(fā)展。
現(xiàn)如今,由于我國(guó)經(jīng)濟(jì)實(shí)力的增強(qiáng),無(wú)論是政府還是民間,都有能力投資興建焚燒廠,錢的事情已不在話下。雖然還有許多人擔(dān)心垃圾水分太高、熱值不夠,但原則上通過(guò)必要的預(yù)處理,還是可以燒起來(lái)的。
雖然“燒得起”、也能“燒起來(lái)”,但焚燒廠要是沒(méi)有足夠的垃圾供給,顯然就沒(méi)有建設(shè)的必要。目前,我國(guó)各種環(huán)境保護(hù)和城市建設(shè)管理法規(guī)都明確要求、倡導(dǎo)或鼓勵(lì)生活垃圾要分類投放、分類運(yùn)輸和最終分類處理,一些中央或地方的法規(guī)政策還在積極嘗試從源頭抑制垃圾的產(chǎn)生(如食物垃圾浪費(fèi)、過(guò)度包裝)。如果這種管理思路落實(shí)得有效,將有至少一半的垃圾,包括廚余有機(jī)物、可回收物、園林廢棄物、建筑垃圾不會(huì)進(jìn)入焚燒廠或填埋場(chǎng),混合垃圾處理設(shè)施的建設(shè)沖動(dòng)就會(huì)大大降低。
當(dāng)然,現(xiàn)實(shí)中很多人認(rèn)為關(guān)于垃圾減量和分類的法規(guī)政策根本不會(huì)對(duì)焚燒構(gòu)成限制,因?yàn)檫@些紙上條文實(shí)際都是虛設(shè)的,充其量也不過(guò)是一種理想宣示而已;真正體現(xiàn)政府意志的是那些給垃圾焚燒設(shè)置的一系列規(guī)劃目標(biāo)、政策優(yōu)惠、電價(jià)補(bǔ)貼等實(shí)實(shí)在在的利好條件。
冷靜地分析,當(dāng)正反政策同時(shí)存在的時(shí)候,那種最大程度適應(yīng)目前社會(huì)狀態(tài),不會(huì)給政府、產(chǎn)業(yè)、公眾帶來(lái)太多“麻煩”的辦法是更具優(yōu)勢(shì)的,那種會(huì)給大家?guī)?lái)改革陣痛的想法是令人討厭的。也就是說(shuō),當(dāng)全社會(huì)的垃圾仍在源源不斷大量產(chǎn)生、混合投放的情況下,為消納混合垃圾而設(shè)計(jì)建設(shè)的焚燒廠是最容易被各方接受的,尤其是負(fù)責(zé)垃圾管理的政府部門;大多數(shù)公眾在沒(méi)有受到直接威脅或信息不充分的情況下,也會(huì)舒坦地保持既有的生活慣性,而無(wú)需做出改變。
令人感慨的是,無(wú)論是30年前還是現(xiàn)在,我們?cè)诶芾砩弦恢币詾閹煹奈鞣桨l(fā)達(dá)國(guó)家卻在對(duì)待焚燒的態(tài)度上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種變化首先發(fā)生在歐盟國(guó)家身上,并體現(xiàn)在其近幾年一系列的法規(guī)政策和高級(jí)政府官員的話語(yǔ)中。
2008年,歐盟委員會(huì)正式發(fā)布了垃圾管理的“框架指令”,明確了垃圾管理對(duì)策應(yīng)遵循優(yōu)先次序原則,即預(yù)防垃圾的產(chǎn)生、重復(fù)使用、循環(huán)利用(包含廚余垃圾的生化處理)優(yōu)先于垃圾焚燒和填埋。這意味著無(wú)論從污染控制、能源節(jié)約,還是資源利用的角度,焚燒與填埋都是較差的選項(xiàng)。雖然至今為止,歐洲的垃圾焚燒廠還很多,焚燒減量的任務(wù)還很重,但優(yōu)先次序原則的確定為歐洲未來(lái)通往“零廢棄”的道路奠定了法律基礎(chǔ)。
2012年,歐盟委員會(huì)又發(fā)布了“歐洲資源效率路線圖”,提出要在2020年以前停止將可回收和可堆肥廢棄物送入焚燒廠,并建議垃圾管理的資金支持也應(yīng)遵循優(yōu)先次序原則,即在循環(huán)利用一端加大投入而不是末端處理。
丹麥和法國(guó)是歐洲垃圾焚燒比率最高的兩個(gè)國(guó)家,都達(dá)到了50%左右。但近期兩國(guó)的政府內(nèi)閣成員都先后發(fā)表了她們積極推動(dòng)減少焚燒的政策立場(chǎng)。2013年,丹麥時(shí)任環(huán)境部長(zhǎng)提出丹麥要循環(huán)利用更多,焚燒更少。2014年,法國(guó)環(huán)境部長(zhǎng)也表示焚燒是過(guò)時(shí)技術(shù),在廢棄物收集和能源轉(zhuǎn)化方面,許多技術(shù)都比垃圾焚燒環(huán)保且合理得多,所以必須通過(guò)強(qiáng)制手段來(lái)停止焚燒垃圾。
如今,許多人都知道污染物的環(huán)境容量是有限的,所以大量焚燒垃圾的社會(huì)終究是不可持續(xù)的。至于焚燒的限度究竟該劃到哪,不僅是歐洲人已經(jīng)在思考的問(wèn)題,也應(yīng)引起國(guó)人的重視。
之前本文已經(jīng)討論過(guò)我國(guó)垃圾焚燒廠二惡英和汞污染的情況,如果進(jìn)一步從環(huán)境容量的角度考慮,情況更令人堪憂。
參照我國(guó)目前的環(huán)評(píng)技術(shù)標(biāo)準(zhǔn),大氣中二惡英濃度的上限是0.6pg TEQ/m3,由此可以認(rèn)為任何在此背景下的額外排放都是不可接受的。而現(xiàn)實(shí)是,在北京、上海、廣州、杭州等大城市,大氣環(huán)境中的二惡英已經(jīng)逼近、甚至超出了這個(gè)上限。雖然已經(jīng)存在的二惡英污染并不都是垃圾焚燒所致,但在環(huán)境容量已趨飽和或已經(jīng)飽和的狀態(tài)下,任何新增污染源都會(huì)增加人們的健康風(fēng)險(xiǎn)。
同樣出于環(huán)境容量及污染物環(huán)境持久性特征的考慮,現(xiàn)有的國(guó)際公約和國(guó)家法規(guī)都明確要求限制垃圾焚燒特征污染物二惡英和汞的排放。《斯德哥爾摩公約》要求,垃圾焚燒作為重點(diǎn)行業(yè),其二惡英排放應(yīng)該逐步減少并最大限度的消除;為此,垃圾管理應(yīng)該優(yōu)先采取不形成和不排放二惡英的技術(shù)措施。《重金屬污染綜合防治“十二五”規(guī)劃》也設(shè)置了這樣的目標(biāo):到“十二五”末,14個(gè)重點(diǎn)省份(包含廣東、江蘇、浙江等垃圾焚燒大省)的汞排放相比2007年降低15%,其他省份不超過(guò)2007年水平。考慮到目前焚燒行業(yè)汞污染的現(xiàn)實(shí)情況,新增焚燒廠及其汞排放將惡化全國(guó)重金屬污染防治的總體形勢(shì)。
環(huán)境容量的限制不僅出現(xiàn)在全國(guó)、乃至地區(qū)性的范圍內(nèi),也適用于局部地方。環(huán)保組織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在垃圾焚燒廠的環(huán)評(píng)報(bào)告中,環(huán)評(píng)單位經(jīng)常不按技術(shù)導(dǎo)則規(guī)定,將新增污染疊加于環(huán)境本底以預(yù)測(cè)環(huán)境變化,這種“疏忽”的客觀結(jié)果就是嚴(yán)重淡化新污染源給周圍環(huán)境帶來(lái)的沖擊。事實(shí)上,不論是高毒性的特征污染物,如二惡英、汞,還是常規(guī)污染物,如大氣顆粒物、氮氧化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硫,許多被環(huán)評(píng)的地方都已無(wú)什么環(huán)境容量可言,任何新增污染,都將繼續(xù)惡化當(dāng)?shù)氐沫h(huán)境和公共健康安全。
參照發(fā)達(dá)國(guó)家的經(jīng)驗(yàn),焚燒廠污染問(wèn)題的控制的確可以通過(guò)高資金和高技術(shù)的投入實(shí)現(xiàn),不然這些地方的公眾也不會(huì)輕易允許焚燒廠的建設(shè)運(yùn)行。但這樣的做法只是將污染問(wèn)題進(jìn)行了轉(zhuǎn)化,其結(jié)果就是溫室氣體排放的增加,加劇氣候變化。以二惡英問(wèn)題為例,要最大限度地消除大氣排放,一方面要實(shí)現(xiàn)垃圾的徹底燃燒以及急速降溫,結(jié)果意味著焚燒廠不僅需要補(bǔ)充更多輔助燃料,還要犧牲產(chǎn)能的利用;另一方面,煙氣越是凈化,飛灰中的二惡英濃度越高,其二次處理仍要耗費(fèi)大量能源。在日本,飛灰無(wú)害化處理的方向是高溫熔融,進(jìn)而制成穩(wěn)定的玻璃體,這種過(guò)程實(shí)則是將焚燒廠的污染問(wèn)題轉(zhuǎn)化成了氣候變化問(wèn)題而已。
最終,無(wú)論是焚燒垃圾本身產(chǎn)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還是二次污染控制引發(fā)的溫室氣體排放,合起來(lái)都將使業(yè)已超常的大氣溫室氣體水平繼續(xù)攀高。而根據(jù)最近國(guó)內(nèi)環(huán)保組織發(fā)布的政策建議,基于垃圾分類的非焚燒處理技術(shù)的氣候變化影響可以小至焚燒發(fā)電的八分之一,在我們的前方的確有更好的低碳發(fā)展道路。
轉(zhuǎn)型階段的初步建議
盡管垃圾管理的未來(lái)并不屬于垃圾焚燒,但垃圾圍城、垃圾圍村的現(xiàn)實(shí)困境是必須面對(duì)的,許多建成垃圾焚燒廠的運(yùn)營(yíng)也不能回避。擺在政府和公眾眼前的真實(shí)課題是如何減輕現(xiàn)有焚燒廠的環(huán)境影響和健康傷害,以及如何達(dá)成共識(shí)切實(shí)向“零廢棄”的理想一步步邁進(jìn)。有如下幾點(diǎn)建議供各方參考:
1. 政府部門立即對(duì)全國(guó)所有垃圾焚燒廠開(kāi)展全面、徹底“體檢”,尤其要查找出那些已經(jīng)被曝光過(guò)的焚燒廠出現(xiàn)問(wèn)題的原因,并督促整改。“體檢”過(guò)程當(dāng)然必須要透明、公開(kāi),這樣既有利于提升焚燒廠運(yùn)營(yíng)水平,又有利于公眾理性認(rèn)知焚燒廠風(fēng)險(xiǎn),并反求自身參與行動(dòng)的可能性;
2. 政府部門需研究建立行之有效的焚燒廠違法、違規(guī)的追責(zé)機(jī)制。短期內(nèi),公眾對(duì)焚燒項(xiàng)目的反對(duì),都源自于對(duì)焚燒廠風(fēng)險(xiǎn)的擔(dān)憂。政府除了通過(guò)提高焚燒廠運(yùn)營(yíng)和污染控制水平外,向公眾作出可以兌現(xiàn)的“意外保障”,才能夠切實(shí)降低公眾積蓄已久的不信任感;
3. 政府部門應(yīng)取消對(duì)垃圾焚燒行業(yè)不合理的政策支持。如果從政府提供公共服務(wù)的角度考慮,應(yīng)該學(xué)習(xí)歐盟,明確垃圾管理對(duì)策優(yōu)先次序原則,并出臺(tái)相應(yīng)的具體措施促進(jìn)垃圾源頭減量、物品重復(fù)使用,以及可回收物和廚余有機(jī)物的循環(huán)利用。相關(guān)措施可優(yōu)先考慮體現(xiàn)在垃圾管理的五年規(guī)劃、循環(huán)經(jīng)濟(jì)促進(jìn)法的落實(shí)、垃圾處理技術(shù)政策、地方法規(guī)等制度修訂上。如果從政府管理行業(yè)的角度考慮,應(yīng)該在堅(jiān)守自身監(jiān)管職責(zé)的基礎(chǔ)上,將焚燒產(chǎn)業(yè)真正推向市場(chǎng),去除補(bǔ)貼和激勵(lì)政策,由市場(chǎng)決定其發(fā)展走向;
4. 各地政府和公眾,尤其是垃圾管理部門和特別關(guān)注垃圾問(wèn)題的市民最好互相主動(dòng)聯(lián)絡(luò)、溝通,一起研究、探討本地中長(zhǎng)期,例如5至10年時(shí)間內(nèi),垃圾填埋和焚燒處理的減量目標(biāo),以及按階段、分步驟逐漸實(shí)施的具體行動(dòng)方案、時(shí)間表和各方職責(zé)。只有直面危機(jī)、達(dá)成共識(shí)、共同行動(dòng),垃圾管理才能走出十年原地踏步的困境;
5. 民間環(huán)保組織或公益組織肯定應(yīng)該發(fā)揮倡導(dǎo)新方向、溝通社會(huì)各方意見(jiàn)、促進(jìn)行動(dòng)共識(shí)的作用。目前,除了繼續(xù)堅(jiān)持公眾宣傳教育、減量和分類試點(diǎn)探索等工作外,實(shí)在不可再躲避垃圾焚燒產(chǎn)生的種種環(huán)境和社會(huì)問(wèn)題,只有更好地監(jiān)督垃圾焚燒,促使其真實(shí)代價(jià)的完整顯現(xiàn),才能為更理想的垃圾管理體系贏得寬廣的未來(lái)。
參考文獻(xiàn)
中國(guó)零廢棄聯(lián)盟:《環(huán)保組織對(duì)<生活垃圾焚燒污染控制標(biāo)準(zhǔn)>二次征求意見(jiàn)稿的意見(jiàn)和建議》,2014年。
趙樹(shù)青、黃文雄、謝力:《我國(guó)生活垃圾焚燒行業(yè)二噁英排放現(xiàn)狀及趨勢(shì)》,《城市管理技術(shù)》,2009年第2期。
蕪湖生態(tài)中心:《中國(guó)122座在運(yùn)行垃圾焚燒廠信息申請(qǐng)公開(kāi)報(bào)告》,2013年。
Yuwen Ni, Haijun Zhang, Su Fan, Xueping Zhang, Qing Zhang, and Jiping Chen, "Emissions of PCDD/Fs from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cinerators in China", Chemosphere, 75 (2009), 1153-1158.
鄧蕓蕓、賈麗娟、殷浩文:《上海地區(qū)土壤二噁英污染狀況調(diào)查》,《環(huán)境與職業(yè)醫(yī)學(xué)》,2008年第4期,第353-359頁(yè)。
Junyu Zheng et.al., “Mercury emission inventory and its spatial acteristic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China”,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Volumes 412-413, 15 December 2011.
Dan Hu et.al., “Mercury emissions from waste combustion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10”,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12(12).
《<生活垃圾焚燒污染控制標(biāo)準(zhǔn)>編制說(shuō)明》(二次征求意見(jiàn)稿),2013年。
湯慶和等:《大型垃圾焚燒廠周邊環(huán)境汞影響的初步調(diào)查》,《環(huán)境科學(xué)》,2005年第1期。
趙宏偉等:《深圳市清水河垃圾焚燒廠周圍地區(qū)優(yōu)勢(shì)植物的汞污染研究》,《環(huán)境科學(xué)》,2009年第9期。
王雄等:《垃圾焚燒發(fā)電廠周邊甲基汞濃度分布特征及風(fēng)險(xiǎn)評(píng)估》,《環(huán)境科學(xué)與技術(shù)》,2013年第10期。
Yingming Li, Guibin Jiang, Yawei Wang, Zongwei Cai, and Qinghua Zhang, "Concentrations, profiles and gas–particle partitioning of polychlorinated dibenzo-p-dioxins and dibenzofurans in the ambient air of Beijing, China",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42 (2008) 2037–2047.
Huiru Li, Jialiang Feng, Guoying Sheng, Senlin Lu, Jiamo Fu, Ping’an Peng, and Ren Man, "The PCDD/F and PBDD/F pollution in the ambient atmosphere of Shanghai, China, Chemosphere, 70 (2008) 576–583.
余莉萍:《廣州大氣中二噁英的濃度分布和幾種典型二噁英排放源的初步研究》(博士論文),中國(guó)科學(xué)院研究生院(廣州地球化學(xué)研究所),2007年。
鞏宏平、劉勁松、潘荷芳、朱國(guó)華、王玲、楊寅森、張珺:《杭州市環(huán)境空氣中二噁英類物質(zhì)檢測(cè)與分析》,《環(huán)境監(jiān)測(cè)管理與技》,2012年第二期,第27-30頁(yè)。
劉永麗:《徐文龍:半數(shù)垃圾焚燒飛灰沒(méi)妥善處理》,中國(guó)固廢網(wǎng),2013年。
磐石環(huán)境與能源研究所:《錯(cuò)誤的激勵(lì): 中國(guó)生活垃圾焚燒發(fā)電與可再生能源電力補(bǔ)貼研究》,2014年。